《烟雨朦胧》
张帝龙
清晨,烟雨朦胧。母亲送幼儿园大班的小外孙去上学。或许是新开学兴奋地过了头,小家伙天还没亮就爬起来,认认真真地收拾着自己的玩具和糖果,把姥姥给他买的贴有“奥特曼”图标的新书包装得满满的,小嘴儿里还不住地嘟嘟囔囔着,说要把好吃的、好玩的带到学校去,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。
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。正在晨读的我,被小外甥的一句话勾起了无限的思绪,十多年的求学之路,三十余年的同窗之谊,一桩桩、一幕幕陈年往事如放电影般交相辉映地展现在眼前,如涓涓细流般在脑海中荡起层层涟漪……

王小红《牧牛图》
三十年前的某一天,也是一个烟雨朦胧的早晨。那一天,我起得特别早,没有让母亲叫,母亲还夸了我,说我长大了。只不过我没有告诉她,我起得早不光是因为长大了,还因为夜里尿了炕。当然,纸是包不住火的,被窝也包不住尿炕的事实,中午回家时母亲就发现了,至于后果,我就不说了,反正第二天上课的时候,屁股已经坐不住板凳了。
那天早晨,外面下着小雨。母亲为我准备了干净的衣服,这件衣服可是没有补丁的呦,我穿在身上甭提有多开心了。母亲还为我缝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书包,一针一线密密匝匝地缝出了一个口袋模样,上面还用红丝线缝了一个大大的五角星……我把母亲用捡酒瓶换来的本子工工整整地放进书包里,然后抱着书包一路跑到学校,虽然到学校时衣服已被雨淋得湿透了,可是怀里的书包却安然无恙。
在我的记忆里,当时不叫幼儿园,而是叫“育红班”,是培育红色接班人的寓意,但不知为什么,“育红班”好像没存在多久就解散了。随后的数年里,我几次转学,颠沛流离,直到三年级时,才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位启蒙老师——刘佩兰,她对我的最大帮助是让我有了自信心。
有一次,我考试得了第一名,她奖励我一个小笔记本,上面还盖了学校的印章。这个本子我始终舍不得使用,一直珍藏在柜子里,每当遇到挫折而迷茫时,都会把它拿出来,抚摸封皮上的字迹和印章,便莫名地充满了能量。
上学,对于我和妹妹来说是无比珍贵的,我们的第一个书包都是母亲用一针一线缝出来的,我们的本子、铅笔、橡皮都是母亲用“破烂换钱”买回来的,所以我们的本子用了正面用反面,铅笔实在握不住了,就在“屁股”后面安个“把手”继续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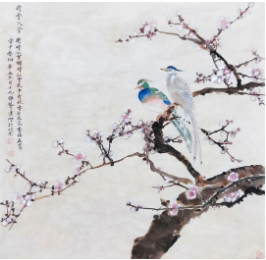
刘汉杰《清香入骨》
那是一个求知若渴的年代,我宁愿对着煤油灯微弱的光线读书,也不愿去跟同伴玩耍而浪费时间。但上学也是有条件的,需要完成一定的任务,那就是利用寒假时间捡粪球,不管牛粪、驴粪还是马粪,只有捡够斤数才能过关。开学时是要过秤的,达不到标准不让上学,直到凑够斤数为止。
那时候,经常在大街上遇到捡粪球的“同行”,见到一坨牛粪比见到黄金还兴奋,呼啦啦一群人拼了命地围拢上去,每个人的眼睛里都冒着绿光,争先恐后,互不相让,所谓谁先抢到就是谁的,这是“行业”规矩,也不知道是谁定的,反正大家都默默地遵守。有时候也会出现特殊的情况,当你发现了“新大陆”,呼哧带喘的冲上前去,却发现牛粪的四周被画了一个大圈圈,这说明已经被人捷足先登了,即便你心中再有不甘,有主之物也不能乱抢,否则就是坏了“规矩”。当然,再多的牛粪也架不住“市场紧俏”,往往是一大堆的“捡粪人”望着光溜溜的路面集体生叹:谁这么勤快?太干净了…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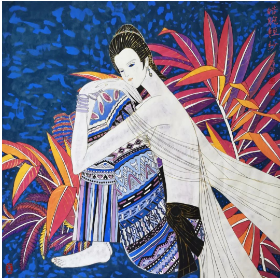
贾筠芳《南国佳丽》
靠捡粪球换取上学的机会,那是物资极度匮乏年代的无奈之举,北大荒的冬天平均零下30多度,学校的取暖主要靠牲畜粪便生火,以有限的煤炭来做辅助,所以才会有这些趣事发生。直到90年代末,牧场学校才盖起了四层楼房,冬季取暖有了充足的煤炭,再也不用学生满大街捡牛粪了。
俗话说,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。如今,时过境迁,我们的家庭条件也今非昔比。小外甥的书包再也不用母亲缝制了,也无需像我和妹妹那样一用就是五六年,他的书包可是一年一换,去年是我给他买的“熊二”书包,今年就变成“奥特曼”了。书包里的本子、多功能文具盒都是我给他买的,再也不用“破烂换钱”了。
为了培养小外甥的兴趣爱好,我们全家都想尽一切办法,给他报了好几个兴趣班,而我则更注重他的文学修养,给他买了很多益智的书籍,尤其是《唐诗三百首》,每天都教他一首,让他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。
出行也不用淋雨了,不管是烟雨朦胧还是滂沱大雨,都不会让他淋着。妹妹每天都会开着轿车过来接他,载着母亲和小外甥一起去上学。
三十多年来,世事变迁,斗转星移,许多往事都已尘封在了历史的长河里,就像深巷子里的一坛老酒,埋在地里慢慢发酵,一旦被挖掘出来,就会散发出醉人的香气,让人陶醉其中,回味无穷。
三十多年来,唯一没变的是我对校园生活的无尽怀念以及对读书的痴迷。上学时,我除了课本里的文章,连课外习题都不放过,还常常到同学家里“借”读,一见到书籍就挪不开脚步。后来,学校有了图书馆,我就把书借回来,先给书包一个书皮,然后净手抄书。我爱书如爱命,读起书来,打雷下雨都听不到,工作以后,我依然坚持每天精读一小时,从书籍中寻找精神的寄托,从优美的词句中感受读书的快乐,我还因此获得了黑龙江省百姓学习之星荣誉称号。因为爱读书,了解的知识也就多,小外甥遇到任何问题我都能为他解答,所以,他至今都把我当作崇拜的偶像……
因为疫情防控常态化原因,今年学校开学也是时断时续,看着小外甥为即将见到学校里的小伙伴而兴奋的样子,竟勾起了我对校园生活的许多记忆。
屈指算来,大学毕业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,离开校园后,再也没有了曾经的天真无邪、无忧无虑,再也无法听到老师的谆谆教诲,只是偶尔还会梦到自己回到了母校,看到那开学第一天升国旗、奏国歌的情景,看到那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校园上空,聆听着校长铿锵有力的开学演讲……
作者简介:
张帝龙,黑龙江省巨浪牧场人,鲁迅文学院作家研修班学员、萧红文学院作家培训班学员,北大荒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散见《中国作家》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《中国农垦》等报刊杂志,并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。现任职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巨浪牧场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。

